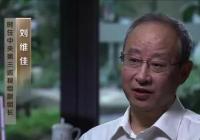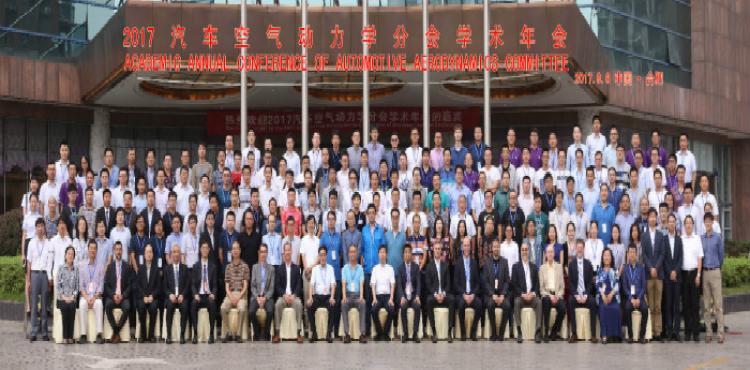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微信公号消息,几乎走进成都的所有书店,在畅销文学分类的显眼位置,都能找到一本叫做《小时候》的书。
这是一本混合着四川方言口语写成的半自传体小说,以类似微博的形式,记录了一个个细节生动的小故事。
是作者一个人的悲喜,更是一群人的集体回忆。
如果你翻开来阅读,会诧异于作者身上近乎于自然的纯真,一直没有失去。无论是何种基调的故事,她似乎都能把它们处理成某种幽默,让人读起发笑。
这本书的作者,是桑格格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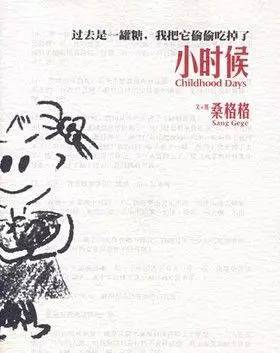
“如果是一个让人觉得心碎的事情,我一定要从里面找到发笑的”,她更喜欢去追求温暖透明的东西,习惯把苦涩埋在欢笑里,把伤心原封不动的搬出来,在她看来过于肤浅。心碎的时候,她从来不写东西。
“这是好多人对写作的误解,认为生活大起大落的时候我们喜欢书写。写作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平衡的状态,一个有距离的事情”,离极端的情绪越远一些,才越能够清晰地审视和回味内心的感受。
“我自己更不是一个能从写作中疏解悲伤的人,我没有这种能力。”
事实上,外人根本不能想象,看起来一直生活在童话里的桑格格,用过了多大的力气,才把那些她没有写出来又萦绕不断的东西渐渐消化。
不够孤独
七八月的杭州,异常炙热,但桑格格仍旧会在每天晚饭前户外运动一小时。有时候慢跑,有时候是散步。这是她自己独处的另一种方式。
杭州是这一两年才搬来的住地,她只告诉了一些朋友。在搬来杭州之前,桑格格常住在北京。
谈及北京,她可以一口气地说出很多个形容词,“粗糙、外放、自由、亲切、历史感”,这些都是她喜欢北京的原因。
“但北京太热闹了。我只想更安静一些,想离热闹的中心远一点”,自我比较成熟以后,桑格格觉得已经不需要外界加的东西,类似隐居的生活状态,是她最满意的,“现在流行的东西我不了解,也丝毫不焦虑”。
桑格格正在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,就是搬到杭州后开始的。
她住在杭州西北部的郊区,因为交通不便,是一个杭州人觉得有些偏僻和单调的地方,桑格格看中的就是这种“隔绝”和“无聊”,“我不需要太多的去了解这个世界,我觉得自己还不够寂寞,还不够孤独,我干嘛让自己变得那么热闹”。
她每天早上醒来,处理完琐事之后开始看书,午睡后,再起来写作,可能写到下午,也可能写到深夜。
这是桑格格为长篇小说做的一个准备。不像之前的随笔创作,长篇小说需要更多的心力,需要更懂得文学的技术活和驾驭文字的能力。
与自己相处,面对孤独,是条件,也是必须。
年初,桑格格停用了朋友圈,只保留了可以选择关注的微博。微博成了她接触外界的一个小小窗口,维持了她社交的基本需求,“我不大喜欢在现实生活中和人社交,对朋友的选择也越来越窄”。

另一方面,她也意识到花过多的时间在社交媒体上,时间和状态太容易被切割。
看手机成为了她不知道怎么面对自己孤独时的一个状态,“如果那天我微博发的比较多,一说明我比较闲,二我比较孤独”。这让桑格格感到相当羞愧。
她给自己立下了条框,例如一两个小时不要碰手机,克制地发布微博,希望在满意的框架内,克制放纵。
有段时间,刻意的戒除手机让桑格格有了“写不出来”的逆反。电脑打开,却没有写,她会倍感压力,甚至一度根本不敢路过家里的电脑。
因为电脑的存在像是一种提醒,提醒你没有使用,浪费了它。她只能绕着它走。
“后来我发现,我这么喜欢手机,那我为什么不用手机写作?既然手机已经离不开了,不如我拿来做正事”,桑格格这部将会出版的长篇小说,初稿大概有十三万字,其中前面的八万字,都是用手机敲出来的。
用手机秘密发个小芽,再移植到电脑上正式写作,这解决了桑格格写小说最大的障碍:畏惧和抗拒。
“拿着手机的时候,你的字就会往下喷,没有一个对文字的畏惧,反而能更好地写下去。如果要用电脑开始去写一个小说开头,对我来说太郑重了。”
快乐或者痛苦
手机消解了电脑的郑重感,随意喷涌的文字,把她拉回到了没有期待,没有压力的时候,像打毛线一般,环环相扣,一次次往下编织。
那是写第一本《小时候》时的状态。《小时候》全书十万字,桑格格花了十天写完,“那时候好像是个原浆,无目的的写作。它不是文学创作,是一个个人经历,我其实以前没有想过当作家,所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。”
《小时候》的文字里,有一种强大的自然的力量,又偶尔显露出早慧的天真和隐忍的幽默感,这种保留着未被阅读影响的原生态语言,使得它不同于其他自述童年的作品,一出版就收获了大批读者。
与通常的作家不同,桑格格的压力很少部分来自于渴望自己的写作被他人理解和认可。
赢得市场的掌声从来不是她的愿望。她希望获得文学意义上的自我肯定。她要做严肃作家。
而市场的反应,扰乱了桑格格无畏的勇气。第一本书的畅销,把她架到了一个为难的状态:“无意间做的一个事情,把你的人生往这边拉,可我又没有做好准备。可因为起点高,大家对你的期待又很大,于是我架那儿了。”
那时候,她对作家这个称号,几乎是躲避的。“这个称号在我心目中,要用相当的努力才能够去赢得和证明。像桂冠一样的东西,别人赠予了我,但我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的”。

她发现在开始走向职业写作后,文学创作不再是“才情喷薄”,而是一次次自由落体后的平静,敏感地感受一切细微的情绪,自己的,他人的,再用极强的理性控制力把自己推出情绪的漩涡,以控制自己在写作时候的距离和张力。
“当初写很快乐,那是原浆。现在其实不快乐。它已经变成一个让你先痛苦,后快乐的事情。”
桑格格再一次提到了对“原浆”的不舍。“我其实非常想留住原来的样子,就像人永远想留住青春,但这是不可能的。你不可能永远把自己封闭原生态当中”。
被迫成长的桑格格,开始了大量的阅读和写作,这两者让她从一个懵懂的、野蛮的、粗放的人变得敏感纤细,
“想写的更好,想让自己处在一个随时都在感受的状态,最后把自己的情绪磨得很细”,而这样高速地高重力使用自己的心智,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濒临失控的状态。
“抑郁其实就是感受力的失控。你越磨越细,你不知道什么是界限,而人各方面其实都是一个极为有限的状态”,抑郁后的桑格格,像潜到黑暗的深海的潜艇,涡轮引擎,高压防水舱却没有足够强大。情绪处在一个摇摇欲坠、支离破碎的状况,感觉仓压要爆掉。
经历过这段痛苦而抑郁的时间,把自己磨得太薄太透,桑格格现在更希望自己变得钝感一些,“我想去努力去做一个冷漠的人”。
敏感和共情带来太多需要额外消化的东西,“比如不要太去在意别人的情绪啊,在冷场的环境泰然自若啊,不要怕尴尬,不要操心所有的事情。
“不过焦虑还是很正常,我一天要焦虑个五六次。每部书都是在这个边缘上挣扎出来的。这种状态,说明你是一种活的状态,你没有写成一个机器,你还在不停怀疑你写出来的东西,写下去的价值”。
和解是一场漫长的精神漂流。远到桑格格会想到地球毁灭。
“一切都会消失,你还去纠结你写的这个东西有没有价值,就太没有价值了。其实你追求的不是价值,是自己是否被别人认可的虚荣心。
其实它不是真正的价值的认定,真正的价值判定要一次次的回到那个原点,就是你想写,你不写活不了,你不写不开心,这就是你写出来的价值,这是一个最大的价值。”
只是她说,自己现在会明白,要一点点地收住保护自己的精力,“以前写得尽兴会通宵地写下去,现在不会了,会收住,像捏住一口气,慢慢来。”
“但只是一点点而已,没有好太多”。
鞭子与绳索
文学创作中,地域是作家塑造笔下人物性格的基础环境。
有些喜欢用一个虚构的地理位置,给自己写的地方定一个调性,马尔克斯的马贡多、鲁迅的鲁镇、福克纳的约克纳帕法,不外乎如此;
有些则写的是那些真实所在,如沈从文写湘西,萧红写呼兰河,而桑格格,写在她生活的地方所看到的一切,提到最多的当然是成都。
但如果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而言,桑格格看起来几乎已经不像是成都人。
方言对她的普通话没有丝毫的影响,声音清亮和语调标准,面对再随意的问题,都带着认真的神色回答。
身上的装束也是低调暗沉,少有耀目的颜色。只有身上露出的白皙皮肤,才让人找到她曾在这座日照辐射极低的城市中生活的蛛丝马迹。

“如果我有下一代,他已经不是成都人,这我想想都会觉得特别难过”。桑格格说自己对成都的感情,比想象的还要深。“而我离成都越远,似乎我越开心”。
提起这个身上重要的这个标签,望着某个点的桑格格,眼神突然有些失焦。故乡对个体产生的拉扯感,在她身上越来越强烈,“我看有个心理学家说,你对异乡越满意,就说明你在故乡可能曾受到过某种压抑”。
离开故乡对于桑格格,与其说是开心,不如说是某种逃离后的轻松。父母的离异,《小时候》里笑中带泪的故事,对于亲历者桑格格来说,是一个不太完善,又真切的童年。
只是在写作以前,早慧却懵懂的她,意识不到这是痛苦。
正式写作之后,她才自觉原来和别人不大一样。
桑格格从小生活在成都的420厂。这个位于成都东边的工厂,曾经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军工企业之一,由1958年从沈阳迁来。
所有人认识所有人。

这更像是一张隐形的网,由很多熟识的目光交织而成。
“我家院子门口,永远有十几个老太太,每次经过,她们都会用尖锐的目光看向我,”别人的婚姻,别家的孩子,全都逃不过桑格格口中“老太太”们的嘴,她们分享着从各处听来的“故事”,作为交换“别处的故事”的谈资。
经过二十多年艰难的转型,如今的420厂除了数千人搬到了新都,大部分已经消失。厂房已被名头各异的房地产商买下,宿舍区也在一块一块被卖出。
能搬走的职工,迁向了成都城的各个角落,仍有一些没有搬走的人坚持留在这里度过余生——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50年。
桑格格的母亲,是其中的一员。而在院子里被打量着成长的“子弟”桑格格,早已走出了这个“大院”15年。
这几乎是不少第三代厂矿子弟的共同选择。
如果从小到大,你都眼看着父辈在必然性与偶然性间,在被动与更加被动之间挣扎,觉得“控制”常常是人世间大多数痛苦的来源,自然也就格外渴望自由。
父辈从五湖四海来,最后的一代人重新散落在五湖四海,“故乡”成了需要自我强化的一个概念。
“甚至在抑郁的时候,我非常怕成都。我回去很多次,却还会有流浪的感觉。我找不到可以呆下来的地方,抑郁的状态会更严重。
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在提醒我,这是你,这是原来的你,这是千丝万缕都想束缚住你的地方”。
事实上,写作之后的敏感,把桑格格突然重新丢回了那个环境,逼她要重新回忆起那些打量的目光和粗鲁的评判,“我非常惊恐”,她后知后觉地感受了小时候的痛苦。
在这种迟到式的痛苦面前,故乡里的大院,好像一根鞭子,曾经抽着桑格格越跑越远,又像是根绳索,永远都没法挣脱。
而正如桑格格说的,你选择成为一个作家,意味着这一辈子你都会在这种与痛苦反复斗争的状态中度日。
原标题:桑格格:我不是一个能从写作中疏解悲伤的人,我没有这种能力
【免责声明】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“来源:上游新闻-重庆晨报”或“上游新闻LOGO、水印的文字、图片、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。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,请与上游新闻联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