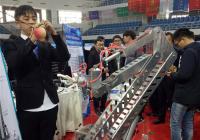澎湃新闻消息,“你明天不用来了。”中年女子走到薛凌云跟前,双手交叉在胸前,抬头看着他说。
“您能告诉我原因吗?”薛凌云低声问她。
“我们员工反映菜不合口味。”女人面色凝重。
薛凌云不再说什么,他已经习惯客户的刁难。2016年,他瞄准团餐市场,开始创业。每个客户签单前,都有三天试吃期。
客户试吃失败后,薛凌云走出知春路银网中心大楼,走进马路对面的吉野家,点了一碗牛肉饭,呼呼地吃起来。
午后两点,约好的三个客户纷纷推迟了见面时间,他坐不住了,决定回家整理公司数据。
旁边就是海淀黄庄地铁站。薛凌云钻进十号线,倒两趟地铁,换到了昌平线。窗外的建筑已从之前的高楼大厦切换到低矮的工业厂房,经过一站地,人群哗地涌出来。
身高1米88的薛凌云也从人群中钻了出来,他将绕过地铁站附近新建的永旺商场和时尚谷,穿过马路,到达北四村。

北京昌平区北四村,一个典型的人口倒挂村。
从中关村到北四村
这是2016年12月底。薛凌云租住的北四村在北京北五环和六环间,是史各庄、定福黄庄、东半壁店、西半壁店的统称,4个村子连成一片,形成一个大型的城中村。
房客们有在中关村和上地上班的小白领,也有农民工、小商贩,这是北五环外一个有名的外来人口聚居区——上一个是唐家岭。2010年,北京市启动唐家岭地区整体拆迁改造工程。在房东们发出搬迁令之后,许多房客在网上贴出转移的新地址:北四村。
按回龙观北四村史各庄村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说法,北四村原村民不过700多户,但截至2016年底,居住总人口达到十多万,其中外来人口占五六万。
进出北四村,大部分租客会经过地铁生命科学园站,它是连接城中村和都市梦的通道,站门口的空地上,密密麻麻地停着换乘的电动车和自行车。
“有句老话叫身大力不亏,在北京不管在哪儿挤地铁,我从来没挤过第二次”,薛凌云一上地铁,通常先把包抱在胸前,手机也搁在包里,下车时,乌压压的人往里挤,里面的人往外推,“如果速度不够快,就只能下站下了”。
他算过,上下地铁晚一趟到目的地就要晚十多分钟,他提醒自己不顾一切往前挤。结果是,挤了几年地铁,挤破了三部手机,屏幕都是毫无征兆地突然裂开。
走出地铁,薛凌云立在寒风中给前同事打电话。“你考虑回北京吗?北京多好。”
挖人没成功,他看起来心事重重,现在公司组建团队,拓展市场,运营营销,全都是一个人在做,压力很大。
2011年,薛凌云从青岛的大学毕业到北京时,身上只装了100元钱。等女朋友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,两人搬进了北四村的三一公寓。那时候一个月工资3500元,房租900元。
第二年冬天,薛凌云和女友领了结婚证,接着他又换了工作,加入一个新兴的互联网公司。从底层销售做起,摸爬滚打两年后,晋升为城市经理。但三年后,公司资金链断裂,走向破产边缘。薛凌云从公司跳了出来,自己单干。创业几年下来,已经发展成七个人的团队。
在北四村住了五年。薛凌云也说不清这里的人是什么时候多起来的。只记得早几年,村里都是破旧的平房,村民开着小夏利在村头趴活儿;现在,“这边的人好多是包租婆和包租公”。
回到像抽屉盒子一样的出租房里,村子外的世界就跟他无关了。这里嗅不出繁华的气息,清一色的灰房子密密匝匝地排列,里面住着形形色色的人,其中就包括年轻白领林雨妍和程序员杨泽。
23岁的林雨妍在上地七街上班,下午五点半下班后,为避开晚高峰,她通常会走一站地到西二旗,再搭地铁回家,路程大约40分钟。
走到村口,她突然感慨:“有时候觉得这个村子的位置很神奇。那边是繁华的商场,这边是村子,中间只隔了一条街。”
前年从安徽合肥一所“不是很好的大学”毕业后,林雨妍到北京培训软件开发业务,培训结束后留在北京找了份产品专员的工作,每月工资六七千。
杨泽比林雨妍早一年来北京。2014年的秋天,他从山西太原大学毕业,来北京找了半个月的工作,最后进了中关村一家“没啥学历和技术要求”的影视制作小公司,每月工资4000,两年半以后,公司就倒闭了。
2016年,杨泽花一万元报了一家计算机培训班,打算向程序员进军。培训班离北四村很近,杨泽庆幸不用挤地铁,看着每天无数人涌向地铁,他感觉“像是一群忙碌的蚂蚁每天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”。

2016年底,杨泽去蓝色港湾过圣诞节。 澎湃新闻记者 周娜 图
彩票人生
如果俯瞰北四村的一天,会看到如潮汐涨落,日夜迥异的景象。
工作日的清晨六点,人流从各个巷道汇聚到北四村的一条无名主街,再涌向生命科学园地铁站;晚上六点到十一点,人流从地铁站涌出,分流回各个巷道,隐没在视野里。天色暗下来,街道两排的商店相继亮起灯,整条街汇成一条灯河。

2016年底的北四村夜景。 澎湃新闻记者 周娜 图
永旺商场入驻前,北四村还是一片片低矮的平房,薛凌云每天都要跨过一个臭水沟子,踩着泥地回村。那时候“摩的”很多,都是加大加长的三轮车或电瓶车,十个人一座,一个人一块。 薛凌云舍不得花这钱,“累坏了才会坐坐”。
在他住在这里的五年里,村里的店铺几易其主,曾经的饭店变成了理发店,理发店再变成副食店。唯一没换的是主街上老张家的馒头店。不过,现在老张的房租翻了一倍,从900元涨到1800元。
星期五的白天,村里的年轻人上班去了,老张和儿子挤在狭窄的门脸里揉面,准备第二天早上的馒头,和他们此时的清冷形成鲜明对比,20米外的彩票店进进出出的都是人。
这是东半壁店村的租客们逗留时间最长的地方了。老板李农兴叼着一根烟说起附近卖手机的年轻女孩,“那小姑娘,往这儿一站,有多少张刮多少张。”据说,她一天刮掉五六百。
下午两点,30岁出头的失业工人阿龙也钻进了彩票店,掏出一百元现金,买了10张“绿翡翠”刮刮乐,坐在凳子上就用啤酒起子刷刷地刮起来。
“选大公鸡的,最高中30万。”李农兴在一旁笑嘻嘻地说。
刮完后,阿龙数了数,中奖的有九张,金额加起来一百元。
“不赚不赔”,他自言自语道。
“老怕输干嘛,来这里就是娱乐”,李农兴说。
“阿龙就指这为生。”店里一个胖乎乎的男人插了一句。
“把我说成啥人了。”阿龙嘟囔着,走到李农兴面前,又掏出十块钱,买了五注大乐透,一屁股坐到开奖机下面。墙上的显示屏上提示着最近一期最高中奖金额是42310元。
大乐透十分钟开一次奖。店里的桌面上,刮过的彩票散了一地。
“姐,再给我来几张。”开奖最后十秒,阿龙吼道。他每个月有大半个月耗在彩票店。此前中过最大的一次是三千块。
阿龙挑选了四个数字后,最后一个数字,“4还是5啊?”他拿不定主意,伸头问旁边的人。那人笑着哼了一声,没回话,“4吧。”阿龙继续自言自语。
店里陆续进来三四个男人。阿龙掏出一支烟,点燃后抽起来。人越来越多,屋子里的烟味越来越浓。
大家热烈地讨论着开奖号码,阿龙皱着眉头。
两个小时过去了,阿龙面前的桌子堆满了猜过的大乐透纸片,他紧紧盯着电脑屏幕上红红绿绿的数字,不时在纸上写下几串数字。
“距离本次开奖还有20秒”,开奖机里再次传出提示音。店里立马安静下来。
阿龙嘴角轻微抽搐着,不知道选择数字9还是10。他最后犹疑地选了一个数字,“7!7!”另一个双颊凹陷的男人大声吼着。“这次一定是11”,前面的数字对上了,店里每个人手里握着几张彩票,脸上带着紧张又兴奋的神色。
所有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墙上的大乐透开奖机,又对了一下手中票上的数字。
“本期中奖号码是2,4,7,9,11。”
“操,差一个数!”
“本期销售结束,马上开奖,祝您好运。”
买了几十注,一次没中,阿龙失望地离开了。从巷子里窜到另一条街上,到李现的副食店买了一包玉溪烟,又钻进另一条巷子里。

北四村的年轻人。澎湃新闻记者 周娜 图
拆迁在即
40岁的李现一个人在店里。前一天,他老婆回了河南老家,照顾14岁的儿子。
在北京待了十来年,李现最早在肖家河那边开杂货店。肖家河拆迁后,他又搬到正白旗,结果又遇上拆迁,“那边房东催说赶快搬家,要拆迁了,挖土机开过来了”。
他只能继续搬家,听人说史各庄的房子便宜,就找过来了。进村一看:街上人挺多,年轻人更多,楼也不少,“肯定得有消费”。他“稀里糊涂”定下了这个落脚地儿,租金一个月1400元,屋内只有一个空架子,他花了两万元买杂货填满这个架子。
李现的杂货店在一个偏僻的胡同里,只有赶上年轻人上下班的时候,才有生意。生意好的时候,一天流水一千多,最差的时候,一天也就两三百。
每周末,村里的年轻人睡到中午12点,起来后都到李现的店里,泡个方便面,吃根火腿肠。不过,他们不怎么跟他搭话,他整日看直播打发时间,“很解闷儿,各式各样的人都有,说什么的都有”,他喜欢跟主播聊天,给对方送免费小花,或者自己花10块钱购买1000块秀币(直播软件上的虚拟货币),再用秀币买鲜花送礼物给喜欢的主播。
李现羡慕北四村的房东,“租房子,收点房租,啥也不用干,不像外地人拼命努力”。他搬过来不久,就听到风声,说北四村要拆了。

昔日北四村夜景。澎湃新闻记者 周娜 图
2016年年底,昌平区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2017年率先启动“北四村”等5个棚户区改造项目的议案。
北京晨报的报道称,随着2009年海淀区唐家岭改造,“北四村”的流动人口开始猛增,不仅人口倒挂严重,“北四村”还被列为市级治安交通消防乱点地区,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。2017年昌平区要完成750万平方米的拆违任务。其中,“北四村”就有300多万平方米。“北四村”拆迁后,将用于生命科学园三期建设。
2017年1月,北京昌平区区长张燕友接受北京晨报采访时称,2016年拆除的城北回龙观市场将作为“北四村”的回迁楼用地,计划在开春后启动建设。
在史各庄的贴吧里,一些年轻租客流露出对拆迁的担忧和焦虑,有人贴出拆迁的新闻,后面跟着一串回帖,“每年年底都是拆迁的新闻,心累”“你们都走我就不用早起坐地铁了”“说两年了,再等两年吧”“别了,史各庄。”
林雨妍在街边看到过北四村附近建设商业中心的规划图,但她没太把拆迁放在心上。“房东什么的都没有说”。
从外观上看,林雨妍租住的三一公寓算得上北四村的“豪华”单间。公寓是由以前的三一重工员工宿舍房改造而来,林雨妍住在三号楼,一共五层,每层住着二十户房客。公寓房租一个月1200,加上“杂七杂八的开销”,每月支出1500元左右。
她的出租房二十平米左右,客厅、卧室、厨房、卫生间都在一个空间里,室内空气不是很通畅,房间里放着一张浅米色布面沙发,白色茶几和衣柜和一张双人床。墙上贴着浅绿色的壁纸。
这间房子是林雨妍和男友装修过的,2015年中秋,他们搬过来后,花了三天时间,“不到三千块”,把室内装扮了下。2016年年底初见她时,她说不想搬离这,带着一丝侥幸,“一时半会儿拆不了,这么多店呢”。
如果真的拆迁了,林雨妍只能往昌平更偏远的地方搬。她身边很多同事或朋友都在北四村结婚生子,他们每天都在讨论买房问题,“即使买,也只能到燕郊了吧”。
薛凌云也算过一笔账,如果搬到市里住,一年开销将近10万元,“在老家都能买套房子了”。
“市内房价一天比一天高,只能往外跑,越远越便宜。”薛凌云之前公司的一个合伙人,拿到投资,也住不起市里,跑到了沙河。“比这还远两站地。”
但到那时,杂货店老板李现不打算“迁徙”了,“市里又进不去,到太偏僻的地方也没啥意思,再拆就回河南了……”

穿过村里逼仄狭窄的巷子,这是一排出租屋。
离开北四村
从村头到村尾,北四村的租金依次排列成一条向下凹陷的抛物线。当杨泽找房子时,沿着这条抛物线走过去,问过二三十家,价格也从九百多降到了五百多。
他的房间在公寓四楼走廊的尽头,每层楼有共用的厕所和浴室。2016年底,第一次见到他时,他和一个初中同学,一个前同事挤在十五平米左右的房间,三个人分摊一个月500元的房租,“对刚过来北京打拼的人算是合理了”,他很知足。
室友都在的时候,他们凑在一起打牌玩游戏,临睡前,杨泽会在手机上再看看学习网页前端技术的视频。
杨泽个性安静,他梦想去腾讯、百度、微软这种大公司,又觉得自己目前能力不足,英语是他“致命的弱点”。培训班的老师也对他说,这个社会更适合个性张扬的人。
半个月前,杨泽的一个初中同学说自己也在北京,俩人约着到颐和园聚一下。见面后一聊,才知道两人都住在北四村。
住在村里,杨泽心里倒没什么落差。每次坐地铁,看着窗外扫过的上地软件园各大型科技公司,网易、百度、联想、IBM,他想的是,“有一天我也会去那里(工作)”。
杨泽计划在北京待五六年,因为“这里到处都是希望”,他已经做好了挤地铁的准备。
而在北京待了五六年的薛凌云正向他的目标加速进军。2016年底,他已经签下了20多家公司的合作,“都是用脚跑出来的”。
刚来北京时,他曾连续一年多早上5点半从北四村的家里出发,搭地铁到团结湖,在大街上发传单做团餐推销,“扎扎实实做好几年才有现在的资源”。
他难以忘记,创业后接到第一单的情景:拿到佣金,“倍儿爽!”
2016年底的一天,薛凌云为2017年立下了个小目标:“明年挣个100万,组建100人团队”。随后,他发了条微信朋友圈,接着又犹豫着,立马删掉了朋友圈。但第二天突然信心爆棚,“为什么做不到?必须做到”,他又发了一遍。
薛凌云几乎天天约客户,谈生意。2016年年初,他坐地铁到国家会议中心见客户,到了目的地后,才发现客户被竞争对手开车接走了。一气之下,他回去和老婆商量,买了一辆几万块钱的二手车。之前租了几个月北京车牌,被人收回去了,新办的山西车牌还没下来,他的车停放在北四村唯一的停车场里,每月140元的停车费。
房间隔音效果不好,空气沉闷,薛凌云喜欢到车里待着,“视野开阔,能看到更多东西”,不过,在北四村的停车场里看出去,只有一排排公寓房。

薛凌云下班后坐在车里。 澎湃新闻记者 周娜 图
北四村,谈不上是家,“算是过渡区”,他现在租的地方40平米左右,两个房间加个走廊,每月1500元,房间里墙壁上贴着儿子的满月照和周岁照片。
在村里租房没有住房合同,房东一个月收一次房租。薛凌云暗自庆幸运气好,住的房子一直没涨价。但他老婆不喜欢这——冬天的暖气不够热,冷风从窗户缝隙灌进来,他们正谋划着搬走。
2016年年底,两人去看了一下橡树湾的房子,9万一平米,溜了一圈,“倍儿漂亮,哎呀买不起啊,得赶紧挣钱啊。”
说完这句话,他突然意识到什么,沉默片刻,挤出一个尴尬的笑容。“我并不是过得不好,只是……”他停住了,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,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。“其实现在很少有人知道我在做什么,还没做出什么成绩,我不想让人知道”。
那时,他也许还有些犹疑,不确定一年后的生活会是怎样——
2017年底,薛凌云挣100万的目标已经实现了,他在河北沧州买了一套房子,但公司的业务都在北京,他打算继续留在这里发展。
半年前,孩子要上幼儿园,全家搬到了新住处,北京昌平区的一套小区房里。搬家没有不舍,“说搬就搬”,只是在北四村住了四五年,一下没有了夜生活,还有点不习惯。
去年培训结束后,杨泽进了一家公司做知识产权销售,最近,拆迁的消息又在租客间流传,他的一个朋友住在西半壁店村,已经接到房东通知,说要拆了。
杨泽也在忙着找房子,他不知道下一个住所会在哪里。

杨泽在村中废墟上打电话。 澎湃新闻记者 周娜 图
原标题:镜相︱北四村的房客们
【免责声明】上游新闻客户端未标有“来源:上游新闻-重庆晨报”或“上游新闻LOGO、水印的文字、图片、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转载稿。如转载稿涉及版权等问题,请与上游新闻联系。